热点:仲裁人工智能化的“技术介入”与阶段性网络法治频道
本篇文章2123字,读完约5分钟
□曾令健
仲裁是现代中国争端处理的重要途径之一。 人工智能很可能会深刻改变法律实践的面貌,仲裁实践也是可能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仲裁是许多法律实践形式中最容易与人工智能技术产生亲和性的行业,毕竟仲裁以高效、机密性高为“生命线”。 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天然的特征,以免泄露如何更有效地推进仲裁程序、如何更好地保障仲裁活动的商业秘密。 那么,现代中国仲裁智能化的现状怎么样呢? 人工智能对仲裁实践的深刻影响体现在哪里,以及如何看待其影响?

进行中的仲裁智能化
实际上,国内外有相当数量的仲裁机构不同程度地“拥抱”仲裁的人工智能化趋势,取得了大小不同的成绩。 总之,大数据、拷贝挖掘、区块链技术和机器学习等对律师及其当事人、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工作人员的影响已经出现,特别是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

从仲裁主体看,人工智能技术对律师和仲裁机构的影响是直接的。 律师通过用大数据观察仲裁员的行为,预测仲裁裁决,为当事人提供更好的咨询建议,制定更好的仲裁战略。 仲裁机构通过引进智能技术,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仲裁员、仲裁秘书和相关人员的员工人数,而且提高了仲裁活动整体的效率、便利性和安全性。 从仲裁活动中,除了律师将大数据用作案件代理的辅助技术外,现代中国仲裁的人工智能化主要体现在仲裁机构程序的运行和管理上,在仲裁程序的推进方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特别是收集立案、程序管理、文件制作

仲裁智能化中的“技术干预”
仲裁的人工智能化乃至法律的人工智能化,本质上是科学技术介入仲裁实践、法律活动。 现代司法以审判员为“活人”,在正视其个人经验、喜怒哀乐、职业素养、价值观的基础上,强调作为社会个人的审判员在规范的制约下进行审判为基础。 仲裁智能化意味着对科学技术法律活动的“入侵”,引起各种紧张和不快。

最先受到冲击的是仲裁智能化的“技术介入”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众所周知,当事人的决策是仲裁,特别是商事仲裁的“灵魂”。 在仲裁程序的运行和管理的“智能化”过程中,追求仲裁的有效推进,确保当事人的意思充分表现出来,不仅是算法设计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而且是“人工智能”和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优先度,特别是当事人的知情权 现在仲裁程序的智能化,仲裁机构及其人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程序管理是第一。 这是因为人工智能与当事人的紧张关系本质上是后者与仲裁机构、仲裁员的冲突、信息表现及协调。

一进来,仲裁智能化的“技术介入”和正当手续。 正当程序是现代司法的“灵魂”,正义不仅应该实现,而且应该以可见的方式实现。 在仲裁实践中,其正当的程序观念是包含当事人意思的自治理念,且占有极其比重。 这也是仲裁程序和诉讼程序的本质区别,前者是私法性质,后者是公法性质。 另外,正当程序还包括各方仲裁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特别是仲裁员通过整合仲裁活动中的各种资料和新闻进行价值的评价和选择。 这些价值的评价和选择一般需要符合社会的通常观念或在特殊情况下进行充分的正当性论证。 “技术干预”是指如何完成这种评价、选择及其合法性的论证,特别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判决。 理论上,根据大数据、拷贝发掘,特别是机器学习,也许可以有规律且稳定地评价世界多方面的东西,但依然停留在理论水平上。 而且,在极端的情况下,很可能来自仲裁员“瞬间”的“正义感”“突发奇想”。 其正当性的基础多来源于裁判者生存的“人”的一维理解和包容,很多情况下很难通过形式逻辑和价值选择充分证明。

仲裁智能化的阶段性
仲裁智能化的迅速发展必须是阶段性的,这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决定。 “拟”人脑思考乃至“超”人脑思考是人工智能的本质。 如何看待这一阶段性与仲裁“技术介入”的关联? 从逻辑上说,与“技术介入”相关的问题基本上可以“阶段性地”说明和处理。 也就是说,智能化完全实现“人脑思考”乃至“超”的思考后,商事纷争及其他纷争可能是公正、利他、高效的“智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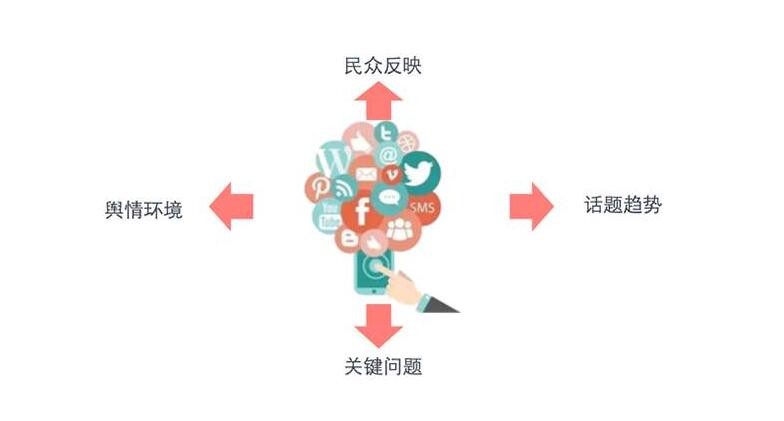
问题又来了,在没有实现人的智能化重建之前,什么样的“技术介入”带来的各种思考如何解答,有比较统一简便的理论解释? 实际上,以前传达的司法也有“技术介入”的问题,只是司法鉴定、专家辅助等程度和方法不同。 关于以前传达的司法、仲裁中的“技术介入”,笔者首先通过理论解释和程序安排排除或避免“技术介入”的司法风险,认为“技术不支配司法。 日本的司法也曾发生过“一件事,两个鉴定”。 关于损害事实与医疗行为的因果关系,两种鉴定的观点完全相反。 审判员在科学上不容易认定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很难说医疗行为在前、损害事实后、两者没有因果关系,在法律上认为因果关系有成立的可能性。 这样通过证据法、导论法的理论和制度安排来规避司法风险,也许可以提供理解仲裁智能化的“阶段性”的观点。

还有学者讨论司法智能化的局限性问题。 这与“阶段性”有关。 不是否定仲裁智能化的界限,不是说不存在界限,而是认为界限问题不值得讨论,实际上“阶段性”本身就是界限问题。 现在讨论仲裁和司法智能化的界限可能太早了,现在最紧迫的是更好地发掘人工智能的仲裁和司法适用,扩大适用界限,客观地看待仲裁智能化的“阶段性”,在此基础上认真对待“技术介入”和由此引起的各种课题

(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标题:热点:仲裁人工智能化的“技术介入”与阶段性网络法治频道 地址:http://www.leixj.com/gy/2021/0320/4213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