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事出有因”未必“情有可原”
本篇文章2794字,读完约7分钟
张田田
西方学者约瑟夫指出,与高度抽象的罗马法等优秀的欧洲人的法律和法律相比,中国的法学从以前就流传下来了,但基本上和想法大不相同。 审理案件多次符合事实,强调妥协与协调”。 ( [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与西方的对话》,劳明译,生活读书高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13—14页)笔者按惯例从事件两方面用清代法制分解过“事件发生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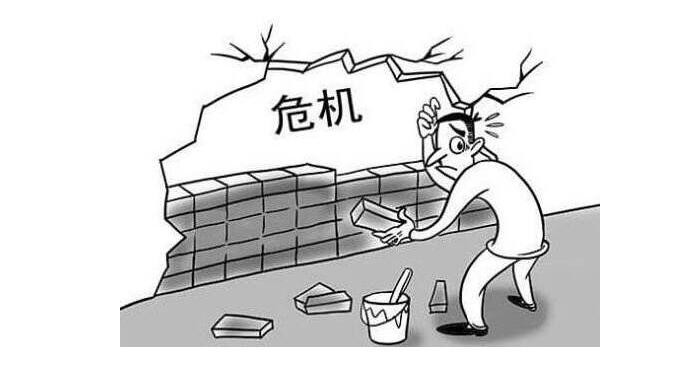
古人听诉讼切断监狱重视“原情”,有其时代背景和变化的过程,中国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在《读史书》中专门讨论了“切断监狱重情”的根源、条件和后世的发展:“惩罚,从意义上来说是事物 得到那份情,悲伤的心一定不能警戒地搬运自己的东西,处罚比不上安德烈吗? 但是,这是国小民可以寡言、俗朴的世界”。 后世的“风俗日漓,民思运”,“不是利害,越来越错误难懂”,“重情”和“诛意”逐渐位于“兼听其意”乃至“诛事”,变成了“依靠法”。 (《吕思勉全集》9《读史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324—326页)阎步克先生在“礼”中概括为“情”重“德”,重“德”。 (阎步克:《医生政治演讲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三版,第78页)但是,总体来说,以前从中国传来的矜持理念和“就业论事”的司法表现,不断持续。 “情理和法有着特别的联系,但中国人似乎也有为了理解法而必须通情达理的特别情意”。 (霍存福:“追求从中国传来的法文化的文化性状和文化-情理法的产生、迅速发展及其命运”、“法制和社会的迅速发展”2001年第3期)霍教授在文章中追溯了儒教的“原情”精神统治下司法中有“情有可原”等。 黄源盛教授通过整理清末民国的刑法修改,指出“矜持”也是近代中国刑法变革的线索。 “晚清以来,介绍以前中国法制中的“可矜可便雅悯”理念,与西方近代法思潮相连”(黄源盛:“从可矜可便雅悯到裁量扣分——)。 从以上观点来看,兼备“情理法”的综合价值评价自古以来就很宝贵,但具体的复印、评价基准并没有停滞,而是与时俱进。

结合清朝刑事案分析“事件有原因”的情况的多与杂。 首先,以“嫌疑人有因”类案件的审理为例,清代审判员遵循一定的规则,其中,在所谓的“有因”为什么会影响刑事责任这一点上,古今的想法不一定一致。 《刑事案汇览》卷四十七载嘉庆二十五年“煽动控制尚未被捕,涉嫌酿成人命”事件一样,秦需要怀疑周继成药死池鱼,指示周泳康宣告周继成,周继成的母亲自尽。 由于有事件的原因,我打算一等减少向人控诉秦得照的致死扭伤罪,并流放”。 所谓“事”,直接应对秦得呼吁周继成的行为,所谓“因”,是秦得怀疑周继成。 并不稀奇。 《沈家本编辑刑事案汇三篇》收到的咸丰元年在山东省发生的“诬告平人导致自杀的原因”事件:有人殴打李某的表妹死亡,有人经过现场,被李某怀疑“在现场挨打”,李某说“语言制作受到了控制”。 刑部司员根据此前秦得案“减死拟流”的判决,此案的李某表示“有嫌疑,事件发生是有原因的,自己按比例减杀模拟……智的成案也再次一致,可以间谍了”,也就是李某也同样被驱逐 这种冤案中的“事件有原因”的“原因”(冤案动机有怀疑、愤怒等)和“事件”(冤案的举动和危害的结果),远远大于现在刑法中危害社会的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清代各级官员在此

其次,《大清法令》规定了部分“事件有原因”、“情有可原”的减刑条件。 判决讲道理时,根据法令斟酌情法,灵活把握。 但是,由于复印件笼统,事件发生了变化,所以办事员有点误解了法律,评价不可避免地错误。 就像《刑事案汇览》卷四十七载嘉庆30年的“重叠诉说母亲重量不轻”事件一样,两江总督报告了事件:嵇层云“诉施远袴监充牙,系统实利”,“诉张荣魁卑役付钱,改变母亲重量”。 在量刑中,江知事故意认为“如果夹着架子撒谎,就应该根据控诉死刑的罪孽进行管教”,但这种层云对张荣魁说“消灭母亲卑鄙”是误解,不是凭空捏造,而是“还有情有据”,所以制定了此方案。 刑部讨论时反驳的主要理由是,层云的犯罪,在心术、手段和影响方面极差:为争夺家园的“微厌”以“中伤伦”的罪名控告张荣魁,“让其背负十恶不容忍之名,立心是最狡猾的”。 “情况计划诉讼7年以上,周转,罗织聚集了很多人,强制统治者,更属于刁健”。 刑部援引嘉庆十三年诏书说:“凡用后置词诉说、轻而重、轻而重的虚词,均不得根据本律处罚。 不要找借口”、“嵇层云根据冤罪判处人死刑未决本律,流杖一百,三千里,加徒刑三年”,也就是说。

从以前流传的中国“原情”“原心”的想法来看,“情有可原”的犯人应该不是非常凶恶、后悔做坏事的一代。 犯法者,如果主观上是“可生可宽”,执行者一定要重视。 正如清代循吏刘衡在《庸吏庸言》中所说,“随便摘水果,律有特别的条件,不能说是小偷。 这个乡的邻居经常看到的事情,情本来是可能的,应该是骄傲的人”。 另外,根据黄六鸿《福惠全书》的卷十二记载,“拟人化的罪恶是最昂贵的原情……强盗抢劫得不到财的情况下,都是切割,没有法律的男性。 但是穷人因为饥饿和寒冷而被迫,无知乡里的愚蠢像匪徒一样被引用,数得着的赃物,衣服不过几件,银不过几件,突然杀了骆驼,不惨! ”。 “法令的设定似乎很严格。 而且看其根据,有非常慷慨的衬衫。 ”这是因为,“一听到重案,考虑到这个方案哪里有轻微的感情,就想到谁有生存之道,有宽广的罪恶,在法令哪里,正好与之相符。 寻求全案轻而易举,是被犯的人追求。 犯的人要求其生可宽,但在法令中要求其相应的救济者,不要与之相适应。 总之求生者宽人阅读”(《福惠全书》卷十八)。 但是,自持和慷慨不是无条件的,“生者宽人”的基础,明确了事实。 如果不是“根据事情原委”,容易缓和强奸。 如上述嘉庆三十年嵇层云冤案,地方官员无法综合权衡犯人的恶性。 “根据嵇层云供给,伊不知道张荣魁的父亲将与嵇姚氏系的再醍醐灌顶结婚。 张荣魁的捐款信封上不刊登姚先生,所以结婚后不能刊登生母。 就像嘉庆十三年敕说的,“法则惩罚申诉人是虚假的等,立法的含义原来是虚假的刁井之徒是善良的,意味着无辜的人犯罪会危害房子,审判明确后, (《嘉庆朝实录》卷一百九十一)

告发死刑者,“告发有原因”不得减刑。 证明处理案件必须区分其“原因”的有无(如《刑事案汇览》卷19中记载的“事畏己藉端”中刑部官员分析立法含义。 罪重者如云,有些“事情发生有原因”,整体上很难“情有可原”。

“国有常刑本来就不允许疏纵。 其或罪可疑,情有可原,介和平又轻又重……必须重复这种诚求。 不要推这种诚求的一颗心。 一定会生气到笔端”(清代张经田《激励治中介》《求生》条)。 根据清代法制,注意“事件有因”和“情有可原”相关规定的共性,反映了案例联合和追求实体正义的理想。 但是,在现实中,根据其本身意义的模糊性和事件的事实、价值评价的多种多样,公平正义的理想的实现总是面临挑战。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标题:热点:“事出有因”未必“情有可原” 地址:http://www.leixj.com/gy/2021/0122/2952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