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中国法文化中的罪与罚
本篇文章3573字,读完约9分钟
韩伟周子焱
罪和罚是法律文化的核心副本,犯罪如何认定,特定犯罪应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自古以来就是法律规范的主要副本,也是依法实现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法学理论、大体、制度和法律用语大量引入国内。 规范罪与罚的刑法也是如此。

与通常的侵害和违反不同,罪恶对人的社会行为是最严重的否定。 在走向文明的社会中,什么样的行为应该成为“罪恶”,古今中外有盗窃、故意杀人等共同的标准,在几乎所有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都被认为是犯罪。 但是,还有很多行为的性质,不那么容易评价,必须结合特定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文化背景加以考虑。 因此,有必要考察中国文化中的“罪”是什么,惩罚是什么,这对我们在中国语境下正确理解罪刑,适用刑法可能有一定的价值。

罪恶的概念进化
一般来说,“罪”的概念出现在秦以后,秦以前多用“辠”,“讲文解字”被解释为“渔竹网”、“辠、犯法”。 清代段玉裁注,始皇在辠字上如皇,变成了“罪”。 墨子注:“辠,犯禁也。” 《尚书》中记载了很多罪与罚的事例,集中出现在《汤誓》、《康诰》、《吕刑》等。 在《汤誓》中称之为“夏多罪,天命死之”。 “夏先生有罪。 害怕上帝,不认为是对的。 ”这位夏先生的“罪”不仅违背了人类的道德和法禁,还包括天理天道意义上的错误,因此商汤为讨伐该罪发誓。 “康诰”是确立“明德慎罚”的大致内容,以“不孝不友”为大罪,区分故意和过失。 “人有小罪,非真,终结,不是自作自受,式尔,晕厥罪小,不可杀。 虽然是小罪,但不是过失,而是没有改变就过的话,必须受到处罚。 如果只想因过失而悔改,即使是大罪也“时间不能杀人”。 “吕刑”列举了五刑、“五过”,强调了关于犯罪要弄清事实。 谕谕给予赦免,其惩罚加倍,念其罪。 ”即,各种处罚必须首先验证其犯罪,同时“上下比罪,无僭辞”。 最终罪重者加重处决,罪轻者减轻处决。 由此明确了定罪量刑的基本基础是“罪轻”,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有疑问的情况下,与通过该犯罪行为确认的处罚相比,减轻了科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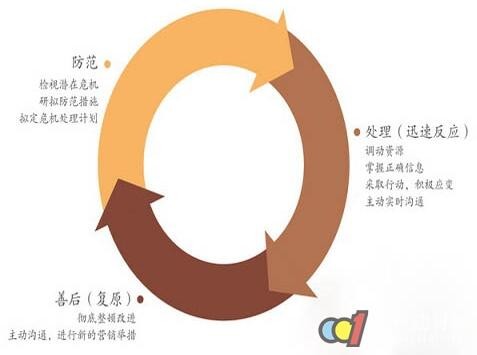
解释儒家经书《春秋》的《左传》第一记述了东周时代各国的大事和重要人物,其中有很多复印件与“罪”有关。 厘公在二十三年,狐狸突然回答公时,罪与“刑”并举,“没有滥用刑,君之明也,也有臣的愿望。 淫刑逞,谁能无罪? ”。 也就是说,罪对刑,刑法制度应该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如果是君主任性任意的“淫刑”,所有人都有可能犯罪。 就像晋侯夷吾想杀瑞克一样,自己居上位是瑞克的功劳,但“为了子弑二君和医生、子君也很难吗? ”。 瑞克理解了。 我只好承认生命。 “我想加罪,那不辞职吗? 臣闻命。 」索性趴着剑死。 还有很多时候,“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点小错,同样是品德不好的晋侯,在国内遭遇饥荒时,秦穆公向秦国觅食,秦穆公看不到他,但读“其君为恶,其民为罪”,依然慷慨晋公。 另外,厘公二十四年,周襄王因王子带之乱出郑,告诉诸侯:“谷差,得罪了母亲弟弟宠子带。” 由于不道德的行为,犯罪或“犯罪”的人,这种“罪”不一定违反法律,但也是违反的。 在《史记》中,“赵敢留下玉壁得罪大王吗? ”。 《呻吟》中的“秦家得罪了万世”同样意味着得罪或相反。 犯罪和“犯罪”的用例在现代生活中依然很常见。

罪与罚之间的联系
在先秦儒家和法家的论说中,罪与罚是联系在一起的。 荀子认为为了减少犯罪,君主首先需要遵守道义,明确名分。 如果人们知道禁止不法行为必然会受到处罚的话,他们会自己认罪并要求处罚“请不要认罪”。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罪刑必须相当。 爵聪明就贵,不当聪明就便宜。 古者不犯罪,子爵不超过德”,“惩罚不愤怒,子爵不超过德”(《荀子君子篇》),惩罚不超过犯下的罪,子爵不超过官员的德行,可以实现想要的“治世”,所以是“惩罚愤怒罪”。 与荀子不同,韩非子说公孙鞅治秦。 “设定坐下来负责,吴也与罪同在,相信报酬丰厚,刑重。 》(《韩非子定法》)这个“罪”当然是违反法令的行为,但其对策是重刑厚奖。 在韩非子的语境中,罪恶也有错误的意思。 “世是不治之症,非下之罪,上失其道。 ”“敬畏罪恶就是胆小。 》(《韩非子诡使》)这里的“罪”,可能也有违法犯罪的因素,但意味着错误和疏漏的情况在增加,“世间不治之症”首先是上位者不能平衡好的名字、利和威的关系。

汉代《盐铁论》中关于罪与刑的很多论述。 “盗伤杀人同罪”、法者、“不设罪陷害人。 》(《盐铁论刑法》)等用例是指违反法禁的行为。 另外,“世界安得不轨的人犯罪了吗? ”的动词。 (《盐铁论周秦》)意思是以此为罪。 《史记》记载了项羽。 “这一天的死是我,也是非战争之罪。 ’错,指过失。 在晋代律学者张斐《注律表》中,“罪”基本上是标准的违反刑法行为,“刑名”是罪法的轻重、“断绝监狱定罪”、“惹人生气等同于人,使法等同于罪”等。 唐律中的“罪”用法相似,“名因罪立,事由犯生”(“唐律疏议名例”)表示罪名设立的大致情况。 “监主加罪”、“制止坐下罪”、“同罪”等指触犯法令的行为,必须受到轻重的处罚。 当然,唐律也有“罪”动词的用法,意味着判决和处罚。 唐代下降,佛教传入,“罪”与佛教经典的戒律、果报有关,形成“罪业”、“罪”等词,它可能不违背国家的律法,但违背佛教的教义,往往同样与特定的伦理道德有关。

宋代理学家朱熹、“二程”等从注释“论语”“子张学干禄”出发,提出了“罪”相关的另一种解释。 后悔了,也有讲道理的人。 ”“虽然重点是说明“尤”,但通过与“懊悔”的对应,也反映了“尤”和罪的一点特征,“懊悔”都含有错误和不当的意思,后者的标准来自内心,衡量“罪”和“尤”。 朱熹批评时说:“被罪福报所迷惑,乐于求报。 丈夫不能让无罪者变直,有罪者要活下来”。 (《朱子语类论刑》)同样指违反法令的行为。 《包郑集》中“水果陷入死罪”、“滥用赃物犯罪者”依然是违法行为的意思。 王守仁论治盗,“抚摸其罪浅”吕坤论要对官员公正。 “罪恶受到不正当攻击,不朴素。 罪恶无理生气,骂则不然。 ”在违反法令的同时,也包括违反礼仪道德的轻微违反。 清末的变法修改法中限制了“罪”的内涵,“大清新刑法”中规定犯罪概念的范围小于“违法”,“法律没有正条,任何行为都不是罪”。 从那时开始就有现代犯罪概念的属性,不再是笼统的违法行为和违反道德的行为。

除罪责任和否定
中国法律文化除了“犯禁”罪外,还有“除责”或“非罪”罪。 也就是说,行为是被禁止的,属于形式上的“罪”,但由于很多理由免除刑事法律责任,进而否定“罪”。 《汉律》中写道:“无缘无故进入人室的家庐舍,乘坐人车船,牵人犯法者,当时格杀勿论,无罪。” 北齐时规定“盗贼群攻击乡邑和入人,杀害是无罪的”。 到了唐代,法律更可靠了。 主人登陆时杀的人,不要论。 ’宅邸、庐舍、车船等,都是居住的地方,有房子,没有主人的同意,别人无权进入。 如果无故入侵,特别是晚上等特殊时间可以给入侵者“格杀”,不被视为犯罪。 此外,“罪”的认定不仅是形式上的“禁止”,还必须结合具体的生活状况,恢复人情常识,无故杀害入侵者,在违反禁止杀人的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在自身和家庭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 除了“无故入人”以外,以类似的形式犯罪,但减轻免责或处罚的,正如研究清代许多刑事案例的美国学者德克布迪注意到的那样,犯罪者因履行家庭义务违反刑法的情况下,必须接受减刑解决。 这也表明,在中国文化中,犯罪和处罚需要在社会道德中加以考虑。

中国现代刑法学家蔡枢机衡分解古文的“辠”和罪,值得提出一些意见观察:罪是“造作”,包括造意、行为及其结果。 罪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禽兽对人类的危害不是罪。 “罪恶是违反统治者禁令和利益的行为”。 从狭义刑法扩张看中国文化中的“罪”,不仅要违反法律规范,还要结合天理、国法、人情来考虑。 最严重的“罪”违背天理天道,夏氏的罪、商汤的罪不被“天命”允许,因此必须受到惩罚,具体的方法包括天罚,或者“革命”。 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罪”是对国家法律的违反,违法犯罪往往受到刑事处罚。 在日常生活中,“罪”可能是指违背社会伦理规范、违背道德、冒犯他人的行为。 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基本上排除了宗教、道德意义,追求“罪”的法定化、客观化,但特定类型的罪的认定和处罚,依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文化的背景。

摘要,中国法律文化中的“罪”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必须在社会道德和伦理关系中定义。 罪、“罪”等词表明“罪”是道德上被否定的行为。 与此相对,基于“防卫”、自保等社会情理的行为不仅不被“责任抵抗”处罚,甚至不被认为是“罪”。 为了人情和伦理,中国语境中的罪主要指人的行为,但动物乃至“人工智能”的行为很难被认定为“罪”,提到要受到处罚。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人文经法学院)
标题:热点:中国法文化中的罪与罚 地址:http://www.leixj.com/gy/2021/0121/29106.html
下一篇:热点:英雄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