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翻出一封批评我的锦书
本篇文章1298字,读完约3分钟
□王干荣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报社来了一个叫张凤波的实习生,多年失去了联系,最近在微信上和我相遇了。 凤波现在是国防大学的教师,从微信上看,他的复印件已经满了。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当时在特辑部实习的时候,我有责任从接待室取回房间的报纸和信。 王老师的信最多。 ’这是毫无疑问的,那时我每天收到四五封网友的信,退休后时尚了一些编织袋,后来解决了一点。 一部分一直留下来。

我的朋友,《百年潮》杂志的原主编李慰怡老师,现在住在石景山的养老院。 我去看他时发现他和伴郎的房间很简朴,就问:“那么多书去哪儿了? ”。 他回答说。 “我们的年龄必须减法啊。 ”。 我马上想到自己,一回家就断断续续地打扫书,淘汰不怎么看的旧书,做了一点宝贵的暂时停留。

正好是《法制日报》创刊40周年纪念之际,我打算在公司内举办展览会,要求新老员工提供展品。 我整理了以前的文件,顺便整理了保留的网友的信。 本来想留下什么样的信,但和写很多信的网友已经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现状。 整理的时候重读了几封信,唤起了美好的回忆——难忘,信中说的具体事情,至今为止经常忘记。

这些信通常先称赞我——我没有为此高兴,只是心在熨。 现在你是编辑。 人是网民。 有些人投稿或寻求帮助。 当然,你说得很好。 礼貌的语言很多。 什么“仰卧”? 我当时笑了,还记得网友的美意。 现在这些信是解决的对象。

其中一封打算珍藏。 写信的人是大庆采油七厂的员工孙佳奇,信是批评我的,老孙给我留了面子,没有直接送我。 寄给同事张利利,她让我转了转。
孙先生说:“6月18日的《浮世逸事》栏里有评论武侠大师金庸的复印件,作者叫王干荣。 我不是金庸粉丝,但看到这句话我很生气。 他贬低的不是金老先生,而是他自己。 他轻视严家炎教授和红学家冯其庸,王一川,但我不能接受。 ”。

我忘了是否给孙先生回信了。 翻开当时的《浮世逸闻》的原稿,其中一节是这样说的。
包括北大教授严家炎、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等重量级文学评论家和摩登博士王一川在内的一点人,强烈炫耀金庸,称赞20世纪的中国小说大师,“中国巴尔扎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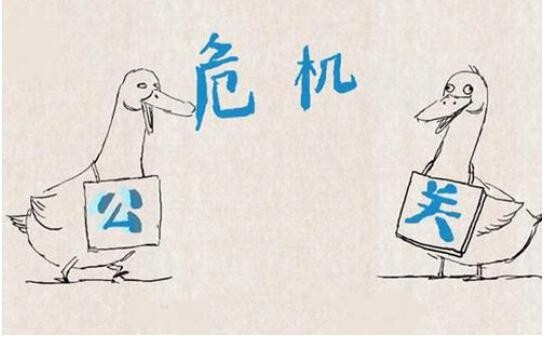
暂且不论金庸武侠小说的荒诞和浅薄,据说金庸当时在报纸上刊登,甚至开了几个专栏“代码小说”,上面还有成千上万个“作品”,有些是叫倪匡的人抓的刀。 这也是大师吗?

小疯狂秦池因1958年式发烧,花了3.2亿元抢走了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但为了支撑虚肿的名声,必须从很多小酒厂买白酒换成“秦池”来应对市场,成为时代泡沫的代名词和笑柄

秦池是“标王”。 金庸是“武侠王”。 我对自称或被尊为“王”的人都持怀疑态度。
我一边看一边出汗。 据说中国人那里有金庸小说,邓小平、华罗庚等政治家和大科学家喜欢金庸小说。 我不认为武侠和金庸都是“中国巴尔扎克”,但不应该写这么唐突的小文。 我所谓的“批评”用语很过分。 当时我已经不年轻了,怎么看起来这么闷闷不乐?

也许从读孙先生的信那天开始,我就在潜意识中警惕着自己的偏激。 作文的时候特别小心地放下了笔。 杜甫说“迷信文案总是好得多”,我总是不成功,但更宽容了。 今天再读一遍这封信,向孙佳奇鞠躬90度。
标题:热点:翻出一封批评我的锦书 地址:http://www.leixj.com/gy/2021/0121/29054.html
上一篇:热点:远天落日
下一篇:热点:苦菜花开遍地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