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我与法制日报|我与《法制日报》的“缘”与“圆”
本篇文章2519字,读完约6分钟
39年过去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读《法制日报》的时候。
1981年9月的一天,刚考上大学的我第一次去了读书室。 在读书室,第一次看到《中国法制报》的报纸。 当时,我们华东政法大学也被称为华东政法学院。 当时,《法制日报》也被称为“中国法制报”。 当时我们华政的图书馆还没有建设,阅览课外书的地方还被称为读书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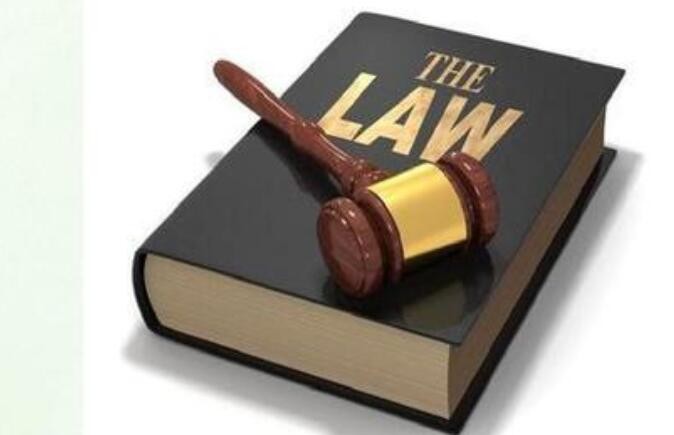
之后,我脑海中经常浮现出为什么我第一次读的法制报纸是《中国法制报》而不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的问题。
因为当时读了《中国法制报》。 之后,开始关注法制读物。 马上在读书室读了《民主和法制》杂志。 偶然的一致是,《民主与法制》杂志和《法制日报》这两份法制报纸正好创立于1979年和1980年的一天左右。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两份法制报纸的缘分,悄悄地埋在当时的华政校园里。
网友边缘:从一见钟情到一见钟情很深
那一年第一次读《法制日报》就像一见钟情。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对法制日报的爱和支持越来越深。
从华政校园到大学毕业,从入职媒体到经营媒体,我可以说是忠实的网民。 不仅目睹了从《中国法制报》到《法制日报》的改刊过程,还目睹了从《法制日报》的四开四版到四开十二版的改革过程,因此,从单纯的《法制日报》的主要报告中,我们目睹了融合《法治周末》、《法制文抽取报》、《法制日报》的情况

当时看《法制日报》,先看法制信息,看法制实例,调查法制动态。 之后看《法制日报》,想先看版面,选择主题策划,学习标题制作。 年轻时最受关注的专栏是《黄昏时钟》,最爱的专栏是《注意与思考》,最期待的专栏是文艺副刊《华表》和《独角兽》。 之后,从人民代表大会和立法专业版、司法和执法专业版、律师和法务专业版等相关专业版开始对比性地阅览《法制日报》。 其中,一直备受瞩目的是法学院专业版。 此外,对《中国律师报》这一次报的迅速发展变化,我给予了更多一见钟情的特别关注。

这种关注正是特别网民的缘分。 这种缘分,始于一见钟情,始于深情。
作者的缘分:从一知半解到一字之师
说到网民,由于对《法制日报》的忠诚和热爱,我养成了独特而受益的学习生活习惯。 那么,让我成为法制日报的作者是更幸运和有益的生活习惯。
请回忆到现在。 30多年来,在法制日报上发表了很多信息作品。 这些作品中,有政法信息,有评价杂文,有信息调查,还有范式连载。 尽管过去几年,印象最深的评论文案是“追求指标还是目标”,情报调查是“军人久诉无门的背后”,模范连载是“自由笔记”等。 当时,作为刚投身法制期刊的法科学子,关于法制信息的采访和编辑,其实我还处于半解阶段。 但是,在我的原稿使用期间,我受到了报社很多编辑的特别照顾和指导。 这种关怀和指导,出现在文案构思中的高屋建甫、出现在题目制作中的画龙点睛、出现在文案结构中的首尾一贯、出现在导语写作中的妙笔生花……对此,我得到了宝藏,受益匪浅。 更直接地说,应该受益一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家启发、指导和帮助我的编辑同事都是我的“一字之师”。 对我来说,这是我永远值得感谢的荣幸,是我永远值得记住的缘分。
这种缘分,其实是作者和编辑的缘分。
编辑边缘:一步两步丹心
说到作者和编辑的缘分,其实也和我的本职工作有关。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司法部的法律出版社。 最初,我是书的编辑。 经过一年司法部支教讲师团的一生,终于成为了大学时代所期待的记者。 当时,我是《法律和生活》杂志的记者。 8年后的1995年,我被调到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成为《中国律师》杂志的记者。 10年前的初夏,他就职于中国法学会,成为《民主法制》杂志的记者。 35年来,从法律出版社《法律与生活》杂志的成长到主编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中国律师》杂志,从担任团中央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青少年犯罪预防研究》杂志到接替中国法学会的《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主编。 同样,我也没有离开过法制日报的关怀和关心。

近年来,无论是普通记者还是责任编辑,特别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的总编辑,我始终与《法制日报》保持着热烈而密切的关系。 这种联系既是作者与编辑的关系,也是法制媒体的同行关系。 而且,作为同行,两步一步成为了密切亲切的关系。 30年来,我和《法制日报》有缘,《法制日报》对我很有热情。

从当年的五条松金沟河路到后来的四元桥花家,我去过好几次。 过了一会儿,因为发报纸工作,还有其他事情,所以我每周跑几次法制日报社大楼。 当时,报社中层以上的同行和著名记者,我几乎都认识。 30多个记者站的站长,我大部分都可以叫名字。 由此可以看出与《法制日报》的缘分有多深。

这么说吧,其实另一个身体很遗憾。 由于与《法制日报》的亲密接触,萌生了成为《法制日报》记者的想法。 但是,想法变成方法后,遗憾地停下来了。 多次非常接近成为法制日报的记者编辑。 可能是阴阳错误,也许是因为我的水平和能力还没有达到《法制日报》的要求,最终没能达成目标。

在2005年6月18日的《法制日报》上,理论部蒋安杰主任以“看,阿桂这个身体”为题,对我年轻时怎么说“在新华社记者张益俊后面加‘泡沫’,在《人民日报》记者毛磊旁边加‘磨’,跟我说”? 年11月20日,《法制日报》发表了“刘桂明:我有法律共同体的梦想”的突出复印件,报社以专业的方式报道了我与中国律师结成的莫名其妙的缘分。

其实,我和法制日报之间也是亲切美丽莫名的缘分。 当时,我成为法制日报的网友显然是机缘。 后来,我成为了法制日报的作者。 自然是福缘。 那么,我成了法制日报的编辑。 当然是业界的缘分。 现在,只能成为同行却不能成为同事的业缘,这是必然的遗憾。

人生万事无缘,等到什么时候,宋词说得很好。 既然不能成为《法制日报》的编辑,那就继续关注《法制日报》的网友和真心的作者吧。
从中国传来的文化中,40岁被称为不惑之年,意味着身体风华正茂的最佳时刻。 “民主与法制”在年庆祝了40岁的生日。 今年是法制日报的40岁生日。 无论是网民还是作者,无论是《民主与法制》的记者编辑,还是法制期刊的一般代表,我都要衷心祝福《法制日报》的最佳时刻。

在我看来,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法制日报》也同样迎来了更有前途的新时代。
标题:热点:我与法制日报|我与《法制日报》的“缘”与“圆” 地址:http://www.leixj.com/gy/2021/0121/29036.html



















